PG电子- 包头塞外乾羽公棚春棚通知
封面图片:184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与日本的地图。欧洲人制作的清代中国地图中,内地与藩部常使用不同颜色。(Dower, John Nicaragua - "China and Japan.PG国际竞猜平台" 1844 World Atlas.PG国际在线娱乐 Henry Teesdale & Co., London.)
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
作者:定宜庄
来源:《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编委会:《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近年来,有关满族“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朝满人是否认同与如何认同‘中国’,这在以往的国内学术界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1,而事实上,国内学术界没有意识到的“不成问题”,恰恰表明了这是以往学术研究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空白和盲点。这个问题首先由美国“新清史”学者提出来,被国内学界视为一种挑战,并由此而引发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回应,所谓“经历过‘新清史’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2这正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美国“新清史”为中国清史研究所做的一个重大贡献。
讨论满族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对满洲作为“民族”的认识;第二个是对“中国”这一名词的理解。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了清朝从建国到覆亡及其以后漫长历史阶段中诸多的本质问题,不可能在一篇小文中进行全面具体的阐释。本文选择晚清到辛亥革命之前这一特定时段,讨论满族在面对这场重大变革时的国家认同,我认为这是讨论满族从有清一代直至如今,其“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却也是往往被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的问题。
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思考
在美国的新清史学者看来,所谓“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具有不同形式、实践和理念的合成体,“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他们认为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所谓“中国”和“中国性”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是多样性的,而非一贯统一的。3
对“中国”等名词的这种认识,是新清史诸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他们对清朝的很多解释,都是从这个基点上阐发出来的,却也是受到国内学界最多质疑之处。如刘凤云、刘文鹏在《“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4一文中所称,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其背后有一个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威权倾向。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质疑。所以,‘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
该文进而又提出:
他们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既然提到了“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的高度,问题便变得严重起来,乃至引起国内许多学者的政治警觉和反击。
事实上,美国“新清史”学者提到的有关“国家”、“民族”的诸多名词,未必如上述引文所说,是来自欧美学界的某种理论或框架,而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人自己在清末直至民国初期曾经历时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经历反复探索求证之后建构出来的基本概念。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革命党人还是君主立宪派,他们撰述的大量文章、专著,以及登载在各种报刊和时论和官方文献等历史资料,都可以用来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对此,说得再明白不过: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5
这两段话中,梁任公明确指出的,就是我国从来都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名”,有的,只是朝廷而已。因为所谓“国家”、“国族”,乃至与之相伴随的“民族”、“种族”的概念,都是近代才出现的,都是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天翻地覆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这些名词才充分概念化,成为西方社会区分人群、解释世界的主要框架。而这些论述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概念范畴,更要到19世纪以后。在中国,这些名词和概念应运而生更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其一,西方各种思想观念已经涌入中国,并对晚清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都是伴随着洋枪大炮侵入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步步紧逼,感受到“亡国灭种”威胁时,才自觉展开了构筑“国族”等一系列活动的。这种其实是晚清以后才被建构出来的“中国”、“中华民族”等概念,其影响之深入人心,以至直到如今,在普通百姓乃至诸多学者心中,都成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不替之论。
由于这些名词所具有的特定的近代性,迄今仍未受到中国清史学界的充分关注,对于西方的民族理论/族群理论,往往也是一头雾水,这便与站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说话的“新清史”学者很难相互理解。6很多学者一谈到清朝皇帝,就以他们多次地、不断地谈到“中国”为证,强调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孰不知在清帝心目中的“中国”或者指代他们的朝廷,或者指代他们占据的领土(亦称“天下”),而全无近代“中国”之含义,与清晚期革命党人或立宪派所称的“中国”风马牛不相及。
梁启超在上述引文中指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共和政体与帝制的区别,指出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帝制之下的臣民与朝廷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区别,可惜的是,有些学者迄今还无法达到当年梁启超等人的认识高度,以至于不断有将清朝与国家的概念混淆不分的现象产生。对此就不更多举例了。这里要说的是,只有对于“国”、“族”指代的究竟是什么,才有可能讨论“认同”这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满族对“中国”是否认同的问题,是一定要置于近代这个特定的语境下,才可能有相互对话的可能性。
二.辛亥革命时期有关满汉关系之争
革命派之所以极力宣扬排满,清廷的腐败无能和对抵抗外敌入侵的软弱消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正当欧洲经历民族主义转型时期,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造成的影响。即如盖尔纳(Emest Gellner)在《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and Nationalism)中所言:“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7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认为是一个民族,便有权在他们居住的领土上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拥有自己的政府,全权治理这个国家。
而中国当时以满洲这个少数民族统治占据多数汉族的清朝,却恰恰违反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原则,这也正如盖尔纳提到的:“违反民族主义有关国家和民族合一的原则,会深深伤害民族主义情绪……对这种情绪伤害最深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裔差异。”8革命党人既然要建立一个单一民族(汉族)的中华国,驱逐其他民族,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满洲,便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至于这样的纲领和主张,到底有多少真的是出于三百年来对满洲统治的民族仇恨,倒反而位居其次了。
要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既然成为纲领,成为原则,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缔造这个“单一民族”,也就是当时人所称的“国族”。始发韧者并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梁启超。早在清亡之前的1901年,他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就呼吁“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得到知识界的群起呼应。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于中国“国族”的塑造,包括提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打造出一个新的国族——汉族,进而构建起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活动,就此而轰轰烈烈地兴起。这一过程曲折复杂且内涵丰富,叙述这一过程又不是本文重点,好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有大量成果出现,这里就不拟多谈了。9
既然建立以黄帝为先祖的单一“国族”已经成为当时的共识,进一步的关键,便是对这个“单一民族”如何解释。晚清知识群体思维活跃,代表不同政见的报刊杂志、社团组织叠出,大分起来,不外主张共和和立宪两种,但在建构国族的一系列问题上,见解却大同小异。
最激进的是革命党人的言论,他们显然是将满洲排除于这个单一的国族之列的,于是才会有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的的《同盟会宣言》提出: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巳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洽,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10
更极端者如邹容,在《革命军》第6章“革命独立之大义”中提出“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一、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一、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一、株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做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其中尤以“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一条为甚。11
立宪派的立场和态度,可以以梁启超与杨度等人的主张为代表。立宪派既然鼓吹君主立宪,而君主偏偏又是革命党人所谓的异族,是应该被革命、被驱逐的对象,只要革命党人的说法成立,满洲君主就只有被推翻而绝无再为君主的理由。因此,梁启超等人与革命党人的争辩,针对的就是汉族单一建国论。
梁启超认为:“国家须有人民,此理之至易明者。但其人民不必有亲族血统之关系,徒以同栖息于一地域,故利害相共,而自然结合,谓之国民。”按照他的意思,只要是同栖息于一个共同地域,利害相共,那么不一定有亲族血统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休戚与共的国民。他认为当时国民所最当努力的是保国,至于保种(汉种)和保教,并非当务之急。同样地,张君劢也说:“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受治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
既然按照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国民”包括了栖息于该地域的所有人,那么,被革命党人排斥于国民之外的“鞑虏”,也就是满、蒙、回等少数民族,是不是也应该列入“国民”之列,又是以何种理由列入呢?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以黄帝为先祖的国族构建呼声几乎压倒一切的时候,梁启超等人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设法为自己的主张寻找根据,而根据的出发点,就是要证明满人与汉族一样,也是中国国民的一部分,这就是“满汉同源论”产生的背景。
他们意图将这块领土之上的少数民族也纳入到“中国”这个共同体之中,即他们所谓的“大民族主义”,以与革命党人主张汉族独立建国的“小民族主义”相对,甚或提倡将“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作为这个国族的族名,如杨度。12对于晚清保皇立宪诸人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学者虽然多所批评,却认为他们力主满汉融合的主要理由,是反对革命,遂使这种批评难以深入。
而这一理论真正的自相混淆之处,是在于他们并没有脱离“单一民族建立国家”的巢臼,只不过将这个“单一民族”加以扩大而已,而未曾意识到,他们的“大民族主义”仍然以汉族为主体,其他少数民族如果留在这个国家之中,是只能“同化”于汉族而没有其他出路的。他们既以“汉化”解释历代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成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也视“汉化”为他们想像出来的“中国”建国的唯一前途。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影响之至深且远,是直到今日仍潜移默化于国人甚至学界中的。

“满人是不是中国人”的激烈争论,正是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发生的。这直接关系到本文的主题即“满族是否有中国认同”,同时也提示给我们,讨论满族的国家认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满族人对“中国”的认同,也不可能是理所当然的、无须讨论的问题。至少在晚清到民国时期,在汉族的“国家”、“国族”建构紧锣密鼓地进行过程中,满族曾有过不被认同为中国人、即使想要加入中国,也必须经历“汉化”之后才会被接受的阶段。
三.辛亥革命前后满族对“中国”的认同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研究成果颇多,本文提到的有关辛亥革命前后知识阶层对“中国”、“国族”的建构过程,内容亦未超出国内外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范围。而我之所以要不惮篇幅地陈述这些概念和过程,是因为若非如此,便无法说清本文以下要重点阐述的问题,那就是,在清朝统治被颠覆的前夜,革命也好,保皇也罢,针对的目标都是一个,那就是满洲的皇室及其臣民,也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而随之而来的以排满为中心并最终推翻清朝的运动,殃及最深的,无疑更是革命的对象、也就是被革命驱逐的“鞑虏”。那么,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中,满人究竟有何反应?有何表现?他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是否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关注、值得探讨的问题。
遗憾的是,许多年来,这个问题却并没有受到充分的注意,作为被革命、被推翻的一方,尤其是要将其“驱逐”出中国的革命宣传占据压倒优势的被动一方,很少人会倾听满人的声音,很少人会关心他们对待这样宣传的态度、立场,包括他们对这个强烈要求将他们驱赶出去的“中国”是否还存“国家认同”的问题。总之,讨论晚清时期满族一方对国族建构、对立宪保皇乃至对“中华民族”问题的立场和表现,是讨论晚清时期满族对中国“国家认同”问题的关键,也正是本文的主旨。
讨论满人在晚清国族建构中的态度和立场,最可靠的途径,是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但在辛亥革命前,可以看到的相关史料很少,本文拟选取几例,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探寻。
1.宗室盛昱的诗
晚清时期的满洲宗室亲贵以保皇党派居多,诸如载涛、毓朗、载泽、善耆、铁良等等,但盛昱可能是个特例。13说他是个特例,缘于他写的一首如今学者多引用来证实满人认同中国的长诗。在这首长诗中,有“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任便”之句,当下有学者称:
这清楚地表明,不但满族人,就连觉罗宗室也心甘情愿地向汉族人的祖先黄帝认祖归宗,向着与汉族同化融合的方向发展。
盛昱强调与汉族同化融合的动因之一,是出于驱逐侵略中华的“白种”异族的政治需要,隐含着明确的近代民族意识。康有为、梁启超大倡融满汉畛域,满汉一家,除了其依靠清帝变法维新的政治立场外,同样具有将国内满、汉、蒙、回、藏等“小民族”合为“大民族”,共同抵御他国异族侵略,保中国,保中华民族免遭灭绝的近代民族意识。14
此时清朝尚未灭亡,盛昱何以竟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向汉族人的祖先黄帝认祖归宗”?何以会有如此前卫的“近代民族意识”?如果不细读全诗,恐怕无法获得一个完整而合理的解释,故不惮烦琐,将全诗引录如次:
《题廉惠卿(泉)补万柳堂图》:15
北人入中土,始自黄炎战。营卫无常处,行国俗未变。
淳维王故地,不同不窋窜。长城绝来往,哑哑南北雁。
耕牧风俗殊,壤地咫尺判。李唐一代贤,代北殷士裸。
辽金干戈兴,岛索主奴怨。真人铁木真,一怒九州奠。
畏吾廉孟子,秀出中州彦。烟波万柳堂,裙屐新荷讌。
《诗》《书》泽最长,胡越形无间。色目多贤才,耦俱散州县。
中州《石田集》,16淮上《廷心传》。终怜右榜人,17不敌怯薛健。18
台阁无仁贤,天下遂畔乱。沙顿亦名家,凄凉归旧院。
文正孔子戒,哲人有先见。至今食旧德,士族江南冠。
孝廉尤绝特,翩翩富文翰。薄宦住京师,故国乔木恋。
堂移柳尚存,憔悴草桥畔。当年歌骤雨,今日车飞电。
绘图属我题,使我生健羡。捉笔意酸辛,铺卷泪凝霰。
我朝起东方,出震日方旦。较似却特家,文治尤纠缦。
岂当有彼我?柯叶九州遍。小哉洪南安,强兮满蒙汉。
闤阓生齿繁,农猎本业断。计臣折扣余,一兵钱一串。
饮泣持还家,当差赎弓箭。乞食不宿饱,弊衣那蔽骭?
壮夫犹可说,市门娇女叹。奴才恣挥霍,一筵金大万。
津门德国兵,镶辉八两半。从龙百战余,幽絷同此难。
异学既公言,邪会真隐患。兴凯入彼界,铁轨松花岸。
北归与南渡,故事皆虚愿。圣人方在御,草茅谁大谏?
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大破旗汉界,谋生皆任便。
能使手中宽,转可头目捍。易世不可言,当时亦清晏。
越肃坟上松,百亩垂条干。万柳补成阴,春城绿一片。
载酒诗人游,嘉树两家擅。”
该诗蕴涵的思想、感情都十分复杂。首先,盛昱的确将“中土”视为自己的国家并且认同,而且将“胡越形无间”、“大破旗汉界”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通篇最突出的却是一种感伤情怀,而不是“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之句表现出的豪情。与盛昱同时代的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说这首诗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显然深解作者之意。
说该诗复杂,首先就表现在“认同”的复杂性。按陈衍所谓“他人”,指的是盛昱所题诗的万柳堂主、以金石书画的收藏家著称的无锡人廉惠卿。廉惠卿曾参加“公车上书”,算得上是个维新派人物,而他之引人瞩目,是因他的妻子吴芝瑛是秋瑾的挚友,也是在秋瑾死后为之营葬的人。但若不是盛昱诗中提到“畏吾廉孟子,秀出中州彦”之句,谁也想不到这个廉惠卿,会是元代著名政治家、畏吾人(约略言之,可说是今维吾尔族的先人)廉希宪的后人。由于廉希宪自幼熟读经书,深通儒家之道,故有“廉孟子”之称。盛昱不仅在诗中点明此事,而且由此而追溯元朝时进入中原的那些色目文人最终未能再归故乡的命运。“终怜右榜人,不敌怯薛健”,按元代选举制度,凡中选的举人和进士都分列二榜:蒙古、色目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一榜,称左榜。右榜人,这里指的就是像廉惠卿和《石田集》作者、蒙古汪古部人马祖常等蒙古、色目文人,他们当时没有“怯薛”也就是蒙古武士、元朝皇室禁卫军的得势,日后散落中原,“薄宦住京师,故国乔木恋”,也仍然保持着对故国的眷恋。盛昱描述他们命运时虽未明言,却用“捉笔意酸辛,铺卷泪凝霰”极言自己酸楚哀伤的心情,他将这些色目文人作为“自己人”来认同并为之洒泪,虽然彼时清朝尚未覆亡,但盛昱似乎已经预感到结局。
该诗后半段直接进入主题,尽述入关后清室由盛转衰的经历,陈衍的评论称:“‘农猎本业断’、‘市门娇女叹’、‘故事皆虚愿’、‘草茅谁大谏’诸韵,皆伤哉言之,”句句讲的都是八旗生计,而八旗生计问题,正是清朝武力衰退的显著征象,可见陈衍是深懂诗人伤痛之所在的。19
至于被当下学者多方引用的“起我黄帝胄”二句,陈衍评说是“仍拘墟之见、过当之言矣”。拘墟,系指井底之蛙,多用来形容见识的浅薄狭隘,显然对盛昱这两句口号式的说法不以为然,或亦如革命派那样痛诋其“彼以异种,自惭形秽,乃托于炎黄之裔,觊觎神州”亦不可知。20但从全诗表达的情感来看,盛昱对于向汉人祖先黄帝的认祖归宗,至少并不像今天有人所看到的那样“心甘情愿”,但是否如沈松侨先生所说,是“企图从‘黄帝’身上,寻得或虚构出一套新的满族祖源记忆,以期消弭满汉畛域于无形”,并且是“假黄帝之符号,启动‘结构性失忆’之机制,试图创造一套新的满族祖源记忆,其目的当然都是在融合满汉,以铸造一个超越满汉族群界限的更大的认同对象--中国国族认同,”我认为也未必有这样明确的意识。总之,此诗并非慷慨激昂的爱国诗,而表现出一种彷徨、无奈和对自己民族命运的深切伤感,反映了一部分满人当时的思想状态,把这种状态说成是心甘情愿地向汉族人的祖先黄帝认祖归宗,未免过于简单,用“找不到北”来形容,也许更确切些。
2.赴日满洲留学生的《大同报》
《大同报》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由留日满洲旗人恒钧、乌泽声等人在东京创刊的,在当时造成一定影响,如今论及辛亥革命前后满人中国认同问题者,无不援引此例,这里似乎已无庸赘言。
《大同报》的发刊词声称,他们的宗旨有四,一为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为主张
乌泽声(1883-?)
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为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为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21在该报存在的短短一年仅出的7期(该报于1908年3月停刊)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现今学者关注并引述的,是乌泽声的长文《满汉问题》。这篇长文中要点有三:
其一,认为满汉已经同化为一个民族。证据是“满与汉,既然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之久,操同一语言、同一土地居住生活、信仰同一宗教,又属于同一种族。”他虽然承认二者间仍然存在某种区别,但这是“同民族异种族”的问题,而“满汉两种人之关系,只问民族,不必问种族,民族既同,斯无种族问题以生也”。
其二,声称反对革命党人的排满,也同样反对清朝廷中某些人的排汉,认为凡居一国土地者,即为一国之国民,继属人主义为属地主义(此语很有趣,属人,即属于某君主或某政权,属地则看居于哪片领土)。鼓吹满汉平等:“故请先求满汉自由、满汉平等……吾所主张之满汉平等分为三类:一军事上平等,二经济上平等,三政治上平等。”
其三,明确主张君主立宪,宣称只有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最适宜的国体:“中国国体,中央权重,幅员辽远,各省不适于生存;中央权微,各省散漫,不适于统一。且蒙古回藏,地僻民僿,不能以自治,必融于中央地方,两权不可偏重。是即中国最适宜之国体而吾所谓单纯统一国体者,即统一内部各行省、外藩蒙回藏成一立宪大帝国之谓也。”乌泽声并特别强调:“即使不辞流血革命,涂炭国民,设立共和政体,势不得不抛弃蒙古回藏,缩小幅员,而后能行民主,是不啻先自瓜分一次,而后建设共和。要知蒙古回藏为中国之土地,其存也可为中国之屏蔽,其亡也能召中国之瓜分,伤一发牵动全身,割一地祸连全体……”
“统一内部各行省、外藩蒙回藏成一立宪大帝国”既是《大同报》的,也是当时鼓吹君主立宪的满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从乌泽声的表述来看,他的基本观念与梁启超、杨度等汉族的立宪派是相同的,其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也与其他立宪章派并无二致。本来,《大同报》诸君就是奉杨度为精神领袖的,杨度在为《大同报》的题辞中,也赞誉该报“尤为自有旗人以来所无之事”,称他们是“旗人中之同志”,可见他们联系之紧密和思想上、政治上表现出的一致性。
不过,如果细察之,在《大同报》的一些文章中,也有不同的表达,可以《中国之排外与排内》一文为例,该文宣称:
统一国者,又谓之联合国,其主义在兼容并包,以张大其国家,异族之来也不排斥之而收容之,岂惟其既来而始收容之,即其未来处于国外之异种人民,且将用手段以牢笼之,用兵力以兼并之,种族虽不纯,而国势固张大无比矣。
至我朝则经略塞外,征回征准,取台湾,数万年相沿相袭,皆挟帝国主义,以联合各异族共立于一国之下,故我中国能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藏,而占地球上五大洲独一无二之亚东大帝国。使当上古时代,循单一国成例,以严斥外族人为主义如黄帝者,只有保守直隶、山峡河南四省,凡此外之人民土地皆以外国视之,皆以夷狄斥之,匪第不能扩其疆宇,恐其固有之疆宇亦不能保守,且日渐剥削,若以之立于今日之优胜劣败之竞争世界中,其必不足以立国也,可断言矣。……大国即强国,强国亦即大国。
今欲排内,是欲以原有之复成国而反欲分离乖隔为一单一国,外人不瓜分我,而我乃自为瓜分,且欲以瓜分召外人,是真不可思议毫无意识之举动也。
该文刊登在1908年第二号上,撰文者佩华,也是《大同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但这篇文章在研究《大同报》的诸文中却较少为人提到,它的尖锐程度,已经超出了其他立宪派人物宣称的满汉融合、满汉同化的比较温和的立场。佩华明确提出,国家若要其张大,就必须兼容并包,如果遵循“单一国”成例,以严斥外族人为主义如黄帝者,将直隶等四省之外的人民土地均以“外国”、“夷狄”视之,在如今的世界上,根本就不能立足。笔者认为,如果谈论《大同报》,这篇文章是不能忽略的。
3.分析
如果仅从《大同报》来看,这些年轻的满洲留日学生对“中国”是有明确的认同感的,他们在当时建构单一民族国家的呼声成为全社会最强音的时期,急切地想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接纳和承认,极力想将自己的民族纳入到这个“中国”之中,为此而希图缩小和淡化满汉间民族差别的存在。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重要前提的,那就是清朝尚未垮台,而这些满洲年轻的知识分子,是将这个朝廷视为自己的国家、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谈论满汉关系的。说到底,这些满族知识分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汉族”的建构对于清朝统治的危险性,但他们能够拿来与之抗衡的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有“君主立宪”而已,只有立宪,只有维持满洲皇帝的统治,才能使这个多元的“中国”帝国免于崩溃,沈松侨先生评价说“他们渴望民族振兴而又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与利益”,可谓一语中的。
《大同报》的创办者,毕竟是一批政治上未必成熟的年轻人,他们的主张,也未必就能代表当时大多数满洲人的意见和态度,杨度在题辞中也说:“大同报社诸同志以少数之人,孤危寡助,力排异议而为之,较吾人之事业尤难”。清亡之后,这些人的立宪理想破灭,他们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政治道路,其中乌泽声和穆都哩(亦名穆儒丐、宁裕之)都曾供职于伪满洲国,穆儒丐的代表作《福昭创业记》追溯祖先的英雄业绩,表现出强烈的满洲民族意识,22我们对这些人在清朝灭亡之后对于“中国”和“黄帝”是否仍然认同、对“满汉同族”说是否仍然坚持,已经无法肯定。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政治立场和态度,已经与清朝未覆亡之前迥异,这深刻地揭示了满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总之,不顾及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语境下的政治立场,来一概而论地对满人的“国家认同”做评价,往往会产生诸多歧义,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再者,即使在清朝未亡之前,在构建单一民族的声音成为主旋律的时候,这些接受维新思想最快的满人中的“开明”者,虽然不得不附合主旋律而高唱民族融合、满汉同源的调子,甚至像盛昱那样将黄帝认作自己的祖宗,但对于“汉化”也仍是有保留的,《大同报》诸君主张满汉同族、满汉平等,但更向往的还是兼容并包的“大帝国”,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与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中国,是有差异的。
纵观以上所举盛昱和《大同报》诸君的例子,可以清晰看出的是,当汉族建构自己“民族”的活动风起云涌之时,虽然清朝尚未解体、满洲皇室也还占有话语霸权,“满洲”或曰“旗人”却既没有建构自己民族的自觉,更没有这种行动。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浪潮,满族知识分子显然既无防备之心,亦无还手之力,表现出来的,是对历史和现实政治在认识上的混乱和叙述上的漏洞百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呈现出模糊和不确定的特点,一旦朝廷覆亡,他们的那些理论主张,倾刻间便烟消云散。下面拟重点讨论的,就是满人之所以会有如此表现的原因。
四.对满族“中国认同”的几点历史思考
1.“满族”构成的复杂性
清朝覆亡之前,革命党人曾力倡汉族独立建国,复兴单一民族的中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种主张如果成为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庞大的清帝国解体,留下一个“主权真空”。至于这个真空由谁填补,从理论上说,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其中一个就是满人也像汉人一样,提出自己的建国纲领,脱离中国而独立。但事实上,尽管在清朝覆亡之后,也有肃亲王等满洲王公贵族妄图效法蒙古这样行事,但就满人的大多数而言,却既不具备自己独立建构民族的条件,也没有这一意识,所以也不存在以分离自立的方式填补这一真空的可能性。何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从满族这个民族的“内因”来看,也许与从初兴时期始就是一个混杂了众多族群和部落、入关后建立的清朝作为一个“帝国”,所具有的多族群、多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样的角度探讨满族形成的历史,或可对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有深一步的了解,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一点,满族与清代的“满洲”(Manchu)不能等同。“满洲”是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所定的族号,而“满族”则是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境内诸多少数民族之一,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予以确立的名称。在此期间,或称“旗人”,或称“旗族”,莫衷一是,且各有各自的特定含义,如果将今天通行的说法运用以清代或者民国时期,都会产生混乱和误解。但为表达简要起见,我们这里也不得不沿用“满族”一称,来指代这个特定的人们共同体。
从历史上看,满族从初兴时期起,就具有特别的复杂性。满族的复杂性,从内部说,在于它的构成。努尔哈齐建立八旗制度,将所有归附人众纳入八旗之下,“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这些人众的构成不仅包括了建州、海西等女真部落,还包括了分布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阔地带的众多“野人女真”部落,以及辽东汉人、蒙古诸部人和朝鲜人等各种人口。皇太极时期又先后建立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待1635年定族号为满洲时,八旗已经是一个囊括了当时东北地区几乎所有不同族群的组织,也使满族这个共同体从建立伊始就具有特别多元的特征。
历经清代,“满族”的成分愈加复杂。八旗制度下的人丁,既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之分,又有内务府包衣旗人和被纳入旗籍的庄头壮丁,满族的各种不同成分,对于被纳于其间(甚或未曾进入)的八旗组织、乃至创造和掌控这个组织的清朝朝廷究竟有没有、又是有着什么样的族群认同,是有很大区别的。举例来说,有清一代被编入八旗户籍的旗地上的庄头、壮丁,保守统计有数十万之众,他们无论居住在辽东还是京畿,都众口一辞地自称为“随旗人”,如今也基本上自报汉族,表明了他们不肯认同于满族的明确立场,是为介乎于满与汉之间的边缘群体。曾参加同盟会,与革命党人一同举行抗清行动的张榕,就属于这个群体。23再如清朝覆亡之后八旗制度随之解体,八旗蒙古的成员大多数认同蒙古族,认同满族的相当罕见。再如很多在清朝曾任显赫高官的汉军旗人后裔,如今也不肯承认自己为满族。所以,在讨论满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时,是不好泛泛而论的。
尽管从康熙朝以降,满人也曾建构过自己的始祖神话和世系,“三仙女传说”和《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问世,就是他们所作一系列努力的起点,但这种努力在乾隆朝之后似乎便呈时断时续之势,究其原因,与“满洲”在八旗内的人数并不呈优势,满洲贵族的统治必须依靠八旗内部非“满洲”血统的各种力量的支持有直接关系。清末维新人士所谓的“汉族”概念,最初就是一个以血缘传承为主的“种族”,满人面对这种建构,处于“找不到北”的状态而呈寂寂无声之势。与这个人群从构成之日起在血缘、地域乃至语言文化上就都具有的多元特点,应该有直接关系。
2.清帝国的多元性
然而,以上征引的《大同报》中佩华的文章,毕竟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该文鼓吹“以联合各异族共立于一国之下,故我中国能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藏,而占地球上五大洲独一无二之亚东大帝国。”鼓吹“统一国者,又谓之联合国,其主义在兼容并包,以张大其国家,异族之来也不排斥之而收容之,岂惟其既来而始收容之,即其未来处于国外之异种人民,且将用手段以牢笼之,用兵力以兼并之,种族虽不纯,而国势固张大无比”,这样的话,很难想像会出自一个当时的汉人之口,而从满人口中说出却自然而然,事实上,这正是清帝国立国原则的写照。
从女真-满初兴时期的外部环境看,建州女真崛起于辽东之时,周边的环境就不单纯。努尔哈齐接受的,固然有来自明朝的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来自蒙古、朝鲜的各种观念和文化。蒙古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对女真-满在文化上的影响源远流长,史有明证,而女真与朝鲜的关系,也早就为王钟翰教授所注意并有所阐述:“在漫长的两个世纪之中,原先在蒙古统治者统治下受过‘万户’封号的居住在当时辽远的依兰地方的这一个女真集团,由于几经迁徙,先去朝鲜,后回中国,不能不受到各方面来的影响”。24这些固然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他们从初兴时期起就面对各种政体、各种文化的情况,使他们与生长在中原汉地儒家社会相对单一环境的汉人存在“先天”的差别,这对他们后来能够建立起多元帝国而不是明朝那样单纯儒家的朝廷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往往被学界忽略。
在晚清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固然也出现了是以文化还是血緣來分辨“民族”的争论,但清代满洲的“文化”与他们的血缘相比,甚至还更多元。盛行于满族初兴时期的萨满信仰早在入关之前就已式微,创建于努尔哈齐和皇太极在位时的满文满语,到乾隆朝以后也已衰落。于是他们的文化,便表现在汉地拜祭孔庙,尊奉儒家学说;在蒙藏地区,又以藏传佛教的虔诚弟子自居。对清政府这种在和不同族群交往中使用不同模式的作法,美国学者柯娇燕将其描述为“并存的皇权”(“simultaneousemperorship”)25,这种宗教上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固然使他们在统治的巅峰时期,可以成功地笼络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上层分子,以维持统治的稳定,却也令人产生了疑问,那就是什么才是他们自己?他们又是凭借什么,来维系这样一个有着众多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帝国中,不同族群对他们的认同?这正是美国“新清史”学者所提出并试图解答的问题,也是他们的着力之点。对此,欧立德(MarkElliot)的论述有一定的代表性:
尽管满洲皇帝展示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每种都有同样的真实性,却代表着不同的权威来源,以及不同的帝国臣民,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满洲皇帝,才能代表这些多元政权,汉人皇帝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正是满洲皇帝的皇统,成为将中国各族群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一旦解纽,满洲族群主权归于终结。
他认为维系这个帝国统治的,是能够代表这些多元文化的皇统,也就是说,皇权是将中国各族群联结在一起的纽带。26
尽管目前中国清史学界对美国“新清史”在政治上构成的“潜在的颠覆性”多所警惕和批判,但如果将“帝国”(empire)作为一个学术名词而非政治术语,清朝是一个帝国而且具有帝国的多元特性,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如果承认这个事实,便也无法无视至高无上的皇统在清朝统治中的作用。总之,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即使能够想像出一个共同祖先,却并不像汉族或者蒙古族、甚至藏族那样,依靠悠久历史和延续几千年的文化来维系,有清一代三百年,维系这个特殊群体存在的,是由皇权统治给予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是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皇权一旦垮台,政治经济基础一旦丧失,茫然不知其所,他们的“认同”也就缺少了一个载体,清末满洲贵族中一部分人拼命鼓吹“立宪”和满汉一家的主要原因,倒未必是这些人特别“开明”所致。
文章写到这里,可以做一个简短但明确的结语,那就是,首先,讨论满族的国家认同,是一个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问题。但只有对两个基本概念达成共识,才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这两个概念,一是何为“民族”尤其是何为“满族”;二是对“中国”的解释,其中又尤以后者最为关键。应该承认的是,在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指代的并非同一概念,尤以清朝与以后的区别为最大,这本应是一个常识。
其次,本文的主旨,是从满族的角度讨论他们对中国的认同问题,选取的则是晚清这个特定时期,在这个特定时期,满人心目中的“中国”与朝廷多少还是重合的,他们对这个中国有着确定无疑的认同,当改良派和革命派众口一辞地鼓吹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时候,他们中一些人的反应,是急切地想加入到这个国家中来,甚至不惜附合汉人而认黄帝为祖,但从切身利害考虑,确实也只有保存皇统、鼓吹“立宪”一途。
总之,对大多数满人来说,清朝的“中国”和清朝被推翻之后的“中国”在他们心目中不可能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从此“中国”到彼“中国”的认同之间的过渡,未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也曾有过痛苦艰难的选择过程,讨论这个过程,是探讨中国现今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关键的一个方面。
注释
1.参见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6页。
2.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载《清史研究》第4期。
3.参见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15页。
4.《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0期4版.
5.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页。
6.参见定宜庄、胡鸿保:《被译介的“新清史”》,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145-155页
7.[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8.同上第1页。
9.其中尤以沈松侨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卷(1977年)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载《政治社会哲学评论》第3期(台北,2002年)最为详尽并最具说服力。
10.引自《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8—70页。
11.《革命军》于1903年6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12.梁启超1903年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清晰地对大民族、小民族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其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载《饮冰室合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71-76页,并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卷(1977年)。
13.盛昱(1850—1899)字伯熙,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三年(1877)进士,授编修、文渊阁校理、国子监祭酒。史称他“因直言进谏,不为朝中所喜,遂请病归家。讨测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
14.王开玺:《晚清的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中华文史网》
15.《郁华阁遗集》卷二,页5-6。按“小万柳堂”旧称廉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是著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无锡人廉惠卿所建,是廉惠卿夫妇的隐居之地。
16.《石田集》15卷,马祖常(1279—1388)撰。祖常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
17.元代选举制度,凡中选的举人和进士都分列二榜:蒙古、色目人一榜,称右榜;汉人、南人一榜,称左榜。

18.怯薛,蒙古和元朝的禁卫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后来发展成为封建制的宫廷军事官僚集团﹐元代官僚阶层的核心部分。
19.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页10。
20.黄节:《黄史?种族书第一》,《国粹学报》,1年1号,页4。
21.《大同报》颇为学界关注,研究成果甚为丰富,参见孙静、李世举:《大同报与晚清满汉融合思想》,载《新闻爱好者》2010年10期;邓丽兰:《种族政治压力下的政治现代性诉求——从《大同报》看满族留日学生的政治认同》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李龙:《另类视野中的满与汉——以满族留日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载《钦州学院学报》2007年4期等。亦见于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
22.可参见刘大先:《民国旗人对于清初历史的一种想象》,载《满族研究》2011年2期。
23.参见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载《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4页。
25.PamelaCrossley,ATranslucentMirror:PG国际中国平台HistoryandIdentityinQingIdeology,P.10–11,296–336.
26.MarkC.Elliott,TheManchuWay:TheEightBannersandEthnicIdentityinLateImperialChina,2001,p.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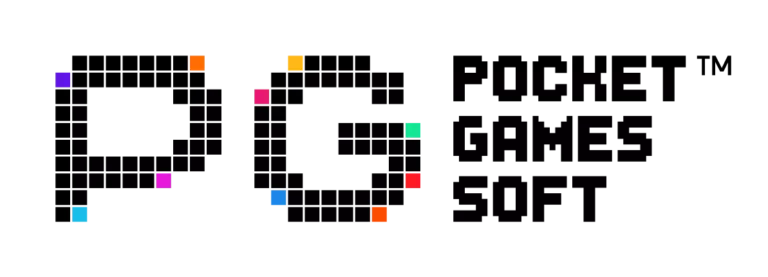
2条评论
Fast shipping and great customer service. Very happy with my purchase.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in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Highly recommend!
Great value for the price. Will definitely buy again.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in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Highly recommend!
发表评论